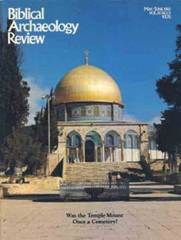历史上的但以理和伯沙撒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11:3,
May/June 1985
张逸萍译自:“Daniel and Belshazzar in History”
By Alan
R. Millard
(https://www.baslibrary.org/biblical-archaeology-review/11/3/4)
晚宴疯狂地进行,美酒畅饮,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站在世界巅峰。地球上没有任何权力可以与巴比伦相比,天上也没有任何神灵可以与她匹敌。
这就是著名的但以理书第五章的背景——伯沙撒盛筵的故事。
我们被告知,伯沙撒王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的后裔。尼布甲尼撒征服了耶路撒冷,摧毁了它的圣殿,夺走了它的财宝。
伯沙撒王喝醉了酒和权势,下令将圣殿里的金银器皿带到他为1000
名大臣举行的筵席上,以便国王和他的大臣、妃嫔和妃嫔可以饮用(但
5 :2)。为什么不把从被征服的寺庙祭坛上取来的杯子和盘子,带到他的皇家狂欢中,以显示他了不起呢?
酒倒满杯,乾杯,巴比伦众神欢呼。喝酒喧闹的人顿时呆住了,眼睛盯著宫墙。 一只手在变白的石膏上写著∶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1]
圣经经文告诉我们∶王“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当然,写的字必须有意义。对于生活被迷信支配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预兆——而且看起来很危险!王害怕了。
他召集了他的哲士和占卜师,并宣布谁能够解释墙上奇怪文字的含义,将在国中位列第三,作为奖励!
巴比伦的哲士被难住了。但以理,这位多年前曾解释过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和异象的犹太流亡者,被召唤并获得同样的奖励,如果他能解释文字的话,他将在国中位列第三。
但以理就这样做了∶伯沙撒王没有在耶和华面前自卑。相反,伯沙撒在耶和华面前自高自大,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
“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但
5:23)。奇怪的话的意思对但以理来说很清楚∶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与玛代人和波斯人。”(但
5∶26-28)。当夜,伯沙撒王被杀。(在“墙上的字”一段中,我们会讨论对巴比伦预兆的解释,以及但以理如何能解释伯沙撒在墙上的文字。)
重现但以理书
5
章所描述的场景只需要一点想像力,因为到处都有同样的狂欢。显然,不寻常的是人们以这种方式使用寺庙中的神圣器皿。即使被俘虏并作为战利品带走,国家圣所的设备通常也会受到尊重。从亚述铭文中的段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从但以理书本身相关的故事的语调也可以。例如,亚述的以撒哈顿(Esarhaddon)说∶“我将被掠夺的神明从亚述送还至他们的神殿”,还有一些文献报导,主前689年,家具以及西拿基立从贝尔马杜克神庙(temple
of Bel-Marduk)移走的雕像,归还巴比伦。[2]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但以理书一直有很多争论。公元一世纪虔诚的犹太人相信它的预言是上帝的启示,死海古卷和新约中的文字,都显示了这一点。死海古卷中有几本但以理书的片段。此外,但以理书的意象充满了昆兰教派的著作。但以理也被新约引用,请参见,例如,马太福音
24:15-16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以及启示录
1:13、4:9
和
9:20。
然而,早在公元
3 世纪,一位腓尼基哲学家,朴腓尼(
Porphyry) 认为,但以理写于主前
165 年左右,远在它所描述的主前
6 世纪的事件之后。随著19世纪圣经批判的兴起,这种观点成为标准。但以理书被认为是主前二世纪的产物,旨在鼓励民族主义和信仰。它关于巴比伦、但以理和各种国王的故事,被认为是虚构的,或者充其量是古老的民间故事,在历史上毫无价值。
当然,尼布甲尼撒统治过巴比伦,但伯沙撒的名字在圣经文本之外无处可寻。保存了古代国王名单的希腊编年史家,将尼布甲尼撒的继任者拿波尼德,确定为巴比伦的最后一位本土统治者;甚至没有提到伯沙撒。1850
年一位名叫费迪南德·希齐格(Ferdinand
Hitzig)的评论员,宣称伯沙撒在显然是一位犹太作家的想像。[3]
然后,在
1854 年,一位名叫泰勒(
J. G. Taylor)
的英国领事,代表大英博物馆探索了伊拉克南部的一些遗址。他挖到了一座巨大的泥砖塔,那是一座主宰城市的月神庙的一部分。泰勒在砖砌中发现了几个小粘土圆柱体,每个圆柱体长约
4 英寸,上面刻有
60
行左右的楔形文字。泰勒把圆柱带回巴格达,展示给他的同事们看。[4]
幸运的是,他的高级同事,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爵士是能破译巴比伦楔形文字的人之一。罗林森能够阅读粘土圆柱体上的文字。
这些铭文是在主前
555 年至主前
539 年巴比伦国王拿波尼德(Nabonidus)的指挥下书写的。国王修复了庙塔,粘土圆柱体是为纪念这事。铭文证明,这座被毁的塔是吾珥城的神殿。这些话是为拿波尼德
和他的长子的长寿和健康祈祷。那个儿子的名字,写得很清楚,是伯沙撒!
这清楚地证明了一个名叫伯沙撒的重要人物,在巴比伦独立的最后几年住在哪儿。所以伯沙撒并不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
然而,这个祷告只提到伯沙撒是国王的长子,而不是国王。
伯沙撒的位置是什么?自
1854 年以来,又出土了几份提到伯沙撒的巴比伦文献。[5]
然而,每次他都是国王的儿子或太子;
他从未在巴比伦语中被称为“国王”。尽管大多数学者现在承认但以理书的作者并没有虚构伯沙撒,但他们仍然断言,圣经作者在称他为国王,是犯大错。
然而,即使这样也可能不太正确。
在主前六世纪的法律契约中,各方根据众所周知的长期惯例向众神和国王宣誓。在拿波尼德统治时期的一些事迹中,我们发现各方都以拿波尼德和国王的儿子伯沙撒发誓。这个以国王和他的儿子名字发誓的实践,在任何其他王朝发现的文件中,都没有得到证实。这表明伯沙撒可能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知道,在他父亲统治的部分时期,伯沙撒是巴比伦的有效权威。巴比伦文献显示拿波尼德是一个有怪脾气的统治者。虽然他没有忽视巴比伦的众神,但他并没有以认可的方式对待它们,并且非常关注另外两个城市,吾珥和哈兰(Harran)的月神。在他统治的几年里,拿波尼德甚至没有住在巴比伦;相反,他留在了阿拉伯北部遥远的泰玛(Teima)绿洲。在此期间,伯沙撒统治巴比伦。
根据一个说法,拿波尼德“将王权托付给伯沙撒”
。[6]
最近的一项发现可能会进一步说明伯沙撒的地位。1979
年,叙利亚北部的一位农民在耕作时,意外发现了一座真人大小的古歌散国王雕像。[7]
雕像的裙边上有两处铭文,一处是亚述文,另一处是亚兰文,两者同时书写,大概在主前
850
年左右。两种不同语言的铭文是平行的,几乎相同,并且每一种都有助于解释另一种。亚述文字描述了在其雕像上的统治者为“歌散的总督”;亚兰文用的字是“国王”(mlk)。每个铭文都针对不同的受众,亚述版本针对封建领主,亚兰文是给当地人的。对于讲亚述语的封建领主来说,是总督,对于当地讲亚兰语的居民来说,相当于国王。这尊雕像上的文字很可能表明,但以理所写的伯沙撒头衔,从亚兰文来说,并不是他巴比伦头衔的字面翻译,即王储。
根据巴比伦的资料和关于这尊雕像的新文本,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让但以理书等非官方记录,称伯沙撒为“王”。他有如国王,他父亲的代理人,尽管他可能不是合法的国王。与但以理书有关的故事中,确切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令人困惑。
正如人们早已认识到的那样,这个提议,可能解决一个对巴比伦哲士和但以理的奖励的难题: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解释墙上的文字,成功的翻译者将“在国中位列第三。”(但
5:16)。为什么是王国的第三位统治者?如果伯沙撒是国王,为什么但以理不能成为他的第二位?约瑟在埃及曾是法老的第二位(创
41:40, 44)。答案可能是:伯沙撒本人就是王国的第二位统治者。如果伯沙撒的父亲拿波尼德真的是国王,那么伯沙撒就仅次于他。
因此,伯沙撒只能给但以理“位列第三”。
吾珥圆柱体和其他巴比伦文献都没有提到“伯沙撒的盛宴”。为此,只有但以理书的证词,虽然我们也有希罗多德(Herodotus)更简单的报导:当古列王的军队在主前
539
年攻占巴比伦时,一个盛宴正在进行中。当然,像这样的考古发现不能证明但以理书中的叙述所报导的事件实际发生在主前
6
世纪,但它们和其他类似的发现,确实表明,这些关于巴比伦的叙述,正确信息被保留下来,而且是发生在应该发生的时候。将但以理的证据视为虚构,或将其贬低为民间传说,就有可能忽略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的力量——的独特来源。
墙上的文字
在巴比伦文化的整个历史中,预兆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试图知道未来的方式。许多聪明的男女,把时间和注意力花在其中。
在古代档案中发现了大量有关预兆的楔形文字板。收集于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著名图书馆的书架上,有关主前
7 世纪中叶的预兆书籍,所占的空间,远远超过有关吉尔伽美(Gilgamesh)甚或创世的故事。尽管在今天,这些预兆并不像其他的故事,那样广为人知,但是花在编译、复制和解释这些预兆集的努力,是巨大的。
几乎任何事物都可能是预兆,是来自众神的兆头,可以引导虔诚者∶动物的活动、怪诞的出生、梦境、升起的烟雾或倒在水面上的油的图案、天体的运行。(其中一些预兆传下来,仍然在我们当中——在十二生肖和流行习俗中,例如观察茶杯底部的茶叶制成的图案。)巴比伦专家注意到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件,并按类别列出,汇编成数千行。预兆可能是好的或坏的。在失败、饥荒或任何类型的悲剧发生之前,所出现的迹象表明,如果再次出现,将会有另一场灾难发生。同样,在胜利、大丰收或其他繁荣时期之前,所观察到的不寻常现象的重现,可能预示著好事。[8]
巴比伦专家对数以千计的不祥征兆进行了分类。每个符号的含义都与符号一起列出; 有些征兆是个人特有的; 其他是国王的; 还有一些对国家或它的敌人。
当伯沙撒要求知道墙上的文字是什么意思时,巴比伦的哲士无疑转向了这些预兆的百科全书。但事实证明它们毫无价值。这些预兆都来自已知事件,或者来自基于已知事物的可能性。例如,一只鹰从东向西飞过城市,然后发生了某些事情,那么如果一只鹰从西向东飞过,则可预测相反的情况,或者如果看到多只鹰飞行,事情可能会加剧。然而,伯沙撒墙上的文字却是全新的。
这超出了巴比伦占卜师们的能力范围。
但以理以巴比伦占卜师的风格解释墙上的文字。眼前所见的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pharsin
是乌法珥新的单数),都是当时在亚兰语中已知的重量名称。墙上写了两遍的弥尼,它是 50
舍客勒(shekel),约
1 ¼
磅。提客勒在亚兰语中相当于舍客勒。乌法珥新是舍客勒的一小部分,也许是一半。这种重量名称的组合,可比作今天写在墙上的美元和美分符号,正是无关紧要的词。
占卜者会通过联想研究这些符号的意义。巴比伦专家们有时试图以玩文字游戏方式,将旧文本应用于当前情况。这就是但以理解开我们故事中的谜团的方法。弥尼与动词“数算”有关;提客勒(希伯来语∶舍客勒)与动词“称重”有关。伯沙撒就这样被数算了或称重了——发现他有亏欠。至于乌法珥新,但以理只是按照这个字的发音,将其解释为波斯人,正如巴比伦专家们也会这样做。因此,波斯人将成为伯沙撒王国的继承人。他们真的这样做了。
根据但以理书
1∶17-20,但以理所得到的教育包括了最先进的巴比伦知识,因此他会知道占卜者的工作方式。他的解释遵循了他们熟悉的方法,所以他们会理解并欣然接受他的解释。的确,伯沙撒就在那天晚上经历了它的真相!
尽管但以理表达信息的方式适合巴比伦人的思想,但但以理的作者不仅仅是巴比伦的专家,他是掌管所有人间事务的天上上帝的仆人。
作者
ALAN MILLARD is
the Rankin Professor Emeritus of Hebrew and Ancient Semitic Languag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and author of Eponyms
of the Assyrian Empire (Eisenbrauns,
1994), Discoveries from Bible Times (Lion
Publishing, 1997) and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Time of Jesus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0), among others.
[1] In upharsin the letter “u” is a transliteration of the Hebrew letter vov. When used as a prefix, vov usually means “and.”
[2] See Morton Cogan, Imperialism and Religion. Assyria, Judah and Israel in the Eigh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B.C.E., SBL Monograph Series 19 (Missoula, Montana: Scholars Press, 1974), Chapter 2, for these and other texts; Alan R. Millard, “Another Babylonian Chronicle Text,” Iraq 26 (1964), pp. 19–23, for the objects from Bel’s temple.
[3] Ferdinand Hitzig, Das Buch Daniel (Leipzig: Weidman, 1850), p. 75.
[4] See E. Sollberger, “Mr. Taylor in Chaldaea,” Anatolian Studies 22 (1972), pp. 129–139.
[5] Raymond R. Dougherty, Nabonidus and Belshazzar: A Study of the Closing Events of the Neo-Babylonian Empire, Yale Oriental Researches 15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9), cites the majority of the texts.
[6] The text is translated by A. L. Oppenheim in J. B.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1969), 313b.
[7] A. Abou-Assaf, P. Bordreuil, Millard, La Statue de Tell Fekherye et son incription bilingue assyro-araméenne, é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Paris: A.D.P.F., 1982). Summary and translation Millard and Bordreuil, “A Statue from Syria with Assyrian and Aramaic Inscriptions,” Biblical Archaeologist 45 (1982), pp. 135–141. See also Adam Mikaya, “Earliest Aramaic Inscription Uncovered in Syria,” BAR 07:04.
[8] A. L. Oppenheim described Babylonian omen-taking in his Ancient Mesopotamia, revised by E. Rein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206–227.
「圣经考古学」主页